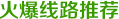大学的类型五花八门:有的能为几乎所有学生提供卓越体验;有的是某种特定类型学生的合适选择;有的则是扼杀学习热情、花钱打水漂的昂贵场所。
此外,有的大学规模不大,师生之间关系亲密,有的则像工厂一样批量产出毕业生;有的大学遵循有效的教学法,还有一些大学只想着怎么提高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的排名……
因此,当你说起“大学”这个词时,要格外注意其潜在含义。那些毕业于名牌大学的成年人,每每回忆起大学时光,总是以怀旧的心情述说着昔日的美好。大学可谓是你第一次真正独立生活,用时间去磨砺日趋成熟的性格。你在大学的快乐与挑战中,结识了一辈子放不下的朋友。你在大学大开眼界,发现了数不尽的有趣思想,脑海深处是永远无法忘却的恶作剧、派对时光、体育比赛和疯狂探险。你的母校,是你身份认知的核心,就像你的服饰、婚礼、遗嘱和誓言一样。大学时光塑造了今天的你,你也认为,每个孩子都理应获得同样的体验。我经常会问一些人,请他们讲一讲大学经历对自己最大的影响。至今为止,还没有一个人回答说,对他们影响最大的是听了哪一堂课。
理查德·阿鲁姆(Richard Arum)和乔西帕·罗克萨(Josipa Roksa)进行的一项富有开创意义的研究,对此进行了解释。这些内容囊括在他们的著作《学海漂流》(Academically Adrift)中。6年时间里,他们跟踪了20多所大学中2300多名大学生的学习情况,发现在完成两年的大学学习之后,“至少45%的学生,在批判性思维、复杂推理和写作技能上,没有统计学上的明显提高”。哪怕是在四年大学学习结束后,上述技能的提高也是极微小的。在此基础之上,他们总结认为,“经‘大学学习评估’(Collegiate Learning Assessment)测评,如今绝大多数学生在接受高等教育的过程中,其一般技能无法获得可测出的提高。”学生之所以什么都学不到,主要是因为大学的教学方法太差,而好莱坞电影《动物屋》就是现如今不少美国大学生学习和品德的真实写照。这些结论与针对雇主的调查结果完全相符,雇主也同样认为,大学并没有让学生准备好迎接日后的职业生涯。毫无疑问,大学生活让许多人发生了蜕变。对于艰苦条件中成长起来的孩子来说,大学更是一处神奇的存在,在让他们大开眼界的同时,还将他们从贫困的命运中拯救了出来。不过,在对大学展开讨论的同时,我们也需要对大学情况的变化有一个清晰而冷静的认识。在上述变化的基础之上,大学理应有充分的动力去提升其价值主张。但事实上,寻求改变实在是难上加难。忠实而慷慨的校友希望自己的母校就像自己搬进新生宿舍的那个秋天一样,永远不要改变;而拥有终身教职的教授们,则对能生存于拥有光荣历史和传统的象牙塔之中感到非常自豪。这些恪守己见的学者常常认为,教书这件事会让人在研究上分心,找不到改变的理由,如果有人持不同意见,那就干脆对其视而不见。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尊重以实践为基础的学习方法,和以项目制学习为中心的大学,诸如西北大学、滑铁卢大学、欧林学院、普渡大学等。斯坦福大学描绘出了一幅关于未来的与众不同的愿景,到那个时候,学生在学校不断精进的将是使命而非专业,学习活动也会在校内学习和真实世界体验之间不断循环。接下来,我们将走进创新大学,看看那里的学生如何学习,学校又是如何在社会的竞技场上帮助维护公平的。亚利桑那州立大学(Arizona State University,简称ASU)的校长迈克尔·克罗(Michael Crow),正在进行美国历史上影响力最大的大学改革工作。亚利桑那州立大学总部位于亚利桑那州坦佩,分校区遍布全美各地,在籍学生数量多达10万。近两年,这所学校被提名为全美最具创新意识的大学,这个说法无可非议。克罗曾担任哥伦比亚大学的教务长,他在ASU任期内,学生数量几乎翻了一番。如今,学生群体的多样性,就像亚利桑那州内的人口结构一样丰富,学生的留校率和毕业率均大幅增长。他将学校“以教师为中心的文化,转变为以学生为中心的文化”。他总是提出“我们为什么来到这里”之类的问题,引发人持续不断的思考。克罗认为,大学的角色是“在社会层面发起变革”,而这也正是他现在所从事的事业。克罗成功的关键,就在于他愿意避开那些对大学质量进行评判的传统衡量指标。他注意到,许多学校因为能拒掉大部分申请人,降低录取率,而感到骄傲,他将这种现象称为“虚假的地位”。而ASU最关注的,就是学生是否能上得了学,是否能上得起学,是否能在学校取得成功。学校在试验线上教学的同时,也意识到,在线内容只能是整个学习框架中的一小部分。这些课程包括大量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和支持,在学生和教师间有大量的面对面交谈或在线交流。课程设计者明白,人们需要参与到与其他人的辩论和互动之中,才能实现真正的学习,而不仅仅是被动地坐在那听讲座或看视频。这种观点与那些对“慕课”趋之若鹜的大学形成鲜明对比。几年前,美国大学界曾掀起一场慕课风潮,结果却不尽如人意。观看讲座视频,每隔几分钟暂停一下,进行几道选择题小测试——这样的学习方法根本没办法带来什么革命性的变化。ASU正在将教学模式从以学生的出勤时间为标准,转变为以学生的实际能力和实际掌握水平为标准,使得学生能够以与自身熟练程度相符的学习进度去挣学分。
学校还创办了十几所跨学科学院,以城市开发、国家安全、可持续能源等社会重大挑战为研究目标,研究资金也实现了大幅增长。如今,学校每年产出的技术专利转让费高达数千万美元。他们还为高中生提供了赚取大学学分的机会。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实现了学术成就、应用型学习和环境多样化的完美结合,并由此得以蓬勃发展。这所大学吸引到的“美国优秀学者”(National Merit Scholar)数量,比任何一所顶尖的州立大学都要多,连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和伯克利分校都只能步其后尘。这所大学培养出来的“富布赖特学者”(Fullbright Scholars)数量超过了许多常春藤盟校。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中,几乎一半的学生都能获得佩尔奖学金,40%的学生是家族中的第一代大学生。备注:富布赖特项目始于20世纪80年代,是由美国资助的国际人才合作交流项目。研究人员、教育家和学生可以通过此项目,前往不同国家交流和学习。今年7月,美国政府宣布将中止中美之间的这一项目。克罗的著作《新型美国大学设计》(Designing the New American University),详细讲述了他在包容度、大学费用合理性和学术创新能力等方面的愿景。尽管他的愿景受到了不少人的攻击,甚至被某些学者用“反面乌托邦”等词汇来形容。但时至今日,已有150多所大学慕名前来访问,以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新型办学模式为榜样。常青州立大学(Evergreen State College)是体验型学习领域的先锋。这所大学成立于1971年,因时任州长丹·埃文斯(Dan Evans)签署的新法案而诞生,也是埃文斯州长在担任公职期间诸多创举之中的一项成果。埃文斯也曾担任过两届美国参议员,为人温和有礼。如今的美国政坛根本找不到如此英明的人物。1977-1983年间,他担任着常青州立大学的第二任校长,从那时起,他便一直关心着这所大学的发展。如今90多岁高龄的埃文斯依然精力旺盛。大多数大学生就读的学校,依然在沿用20世纪的教学风格讲课。学校将独立的课程和彼此不相关的学科组织在一起,就形成了某个专业。上完这个专业规定的课程,就能换一张毕业证书。
但人生却并非如此,无法任由我们精细地划分和组织。人生是复杂而凌乱的,你永远也不可能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在常青州立大学,我们有协作式学习项目,学生可以参与到自身教育路径的设计中来。灵活而有机的学生小组,积极而投入的教学团队,所有这些汇集在一起,可以很好地帮助学生为迎接未来的人生做准备。常青州立大学刚成立没多久的时候,曾接到过一位家长的电话。当时,这位家长的儿子刚刚入学没多久,父亲问儿子:“你在学校都上什么课了?”儿子答:“航海。”父亲接着说:“航海挺好,还有什么课?”儿子答:“没了。”父亲听到后大怒,在电话里质问埃文斯:“常青州立大学到底在搞什么?”孩子在一个小规模学生团队里与四位教师紧密合作,他们每天都要进行密集的研讨,话题围绕与海洋有关的文学;
此外,与海洋商业有关的经济学,与风力推动船只在水中行进有关的数学和物理学,以及与海洋探险有关的历史展开;学生们在以真实世界为背景,同时学习5门学科及其相互之间的关联。直到今天,常青州立大学依然承诺为学生提供经济上可负担,能改变人生的大学体验。本州学生的学费只要6300美元,只要申请,基本上都能被录取。
学校为学生提供极大的灵活性,既可以住校,也可以走读。学生若想掌握一门外语,可以到国外去取得属于自己的学习体验;学生若对某个领域感兴趣,也可以走出校门,到社会上去争取真实的学习体验。学校不断寻找新方式,将其他类型的学习转换为学分,无论是在另一所大学上过的课,还是在企业里面打过的工,都可以记为本校学分。学生如果决定暂时从大学学业的正常轨道上脱离出来,无论是几个月还是几年的时间,回归校园时都不会面临官僚程序的繁文缛节。一些令人尊敬的学校,会在先进教学法和贫困学生奖学金上投入大量资源,还有一些学校则将资金主要用在装修学生宿舍,建设豪华校园、体育场馆,购买私人飞机,以及一切能将学校在《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上的排名往前提升的活动上。
许多学生4年后无法毕业,就因为有一两门必修课没完成,而这也进一步增加了他们的大学成本。有些大学为了增加额外收入,对环境更好的宿舍标价更高,还推出了不同档次的食堂套餐,而无视这样的政策会进一步拉大富裕学生和低收入学生之间的鸿沟。
赫布·施罗德(Herb Schroeder)是一所顶尖大学工程系领导,备受人们尊敬。施罗德有着非常曲折的职业发展路线,他在芝加哥度过了自己的高中时代。高二时,他的数学考试成绩不及格,老师便断言说,他这辈子绝对不可能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有什么建树。于是,27岁之前,施罗德再也没惦记过与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相关的任何事情。高中毕业之后,他独自向北闯荡,来到阿拉斯加州,在跨阿拉斯加输油管线的工地找了一份建筑工人的活计。做着做着,施罗德对工程产生了兴趣,于是考上了阿拉斯加大学,在那里拿到了机械工程的学士学位,后又获得土木工程专业硕士和博士学位。一路走来,他经历了太多。回顾自己的学习生涯,施罗德认为,目前学校讲授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方式根本不合情理。而他会给学生提出宏大的设计挑战,比如在设计指标限制下建设一座桥梁;利用当地垃圾场里捡来的部件,设计出一个能撑起一把伞的装置;利用基本的电子元件,做出一个能飞起来的四轴飞行器等。总之,调动学生的积极性,不断给学生提出新挑战,培养学生对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的热情和实际能力。慢慢的,施罗德逐渐意识到一个问题,那就是阿拉斯加本地人很少会选择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作为学术和职业发展方向。怀着对这个问题的好奇,施罗德观察发现,许多本地人上大学时基本的阅读和数学水平都非常落后。高中阶段的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课老师,都很怀疑本地学生是否有能力承担富有挑战的学术任务。因此,许多本地孩子在长到18岁时,都深信自己未来不可能在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有所建树,就像当年的施罗德一样。
于是,在施罗德的倡议下,阿拉斯加本土科学与工程项目(Alaska Native Scienceand Engineering Program)成立了。因为这件事,持反对意见的人“差点把我赶出阿拉斯加”。如今,阿拉斯加本土科学与工程项目已经成功运营22年,为社会输送了400多名拥有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学位的阿拉斯加本地毕业生,还有2000多名从小学六年级到博士生的后备力量。目前,施罗德正在将项目的覆盖范围扩展到非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领域,并向下延伸到初中和高中的阿拉斯加本地学生。他要向世人宣布,阿拉斯加本地孩子的能力丝毫不逊于其他人,他们也可以成为科学家和工程师。同时施罗德也告诉我说:“直到现在依然有许多人对我们的方法提出质疑。许多教育者和家长依然不愿意脱离传统的教育模式,不愿意接纳我们的方法。”无论如何,我们需要关注的是富有创造力和创新意识的教师,真理掌握在他们手里,而不在那些站在金字塔顶尖上发号施令的人手中。正是教师打造出了一间间充满生机的教室,帮助孩子们在里面茁壮成长,不断寻找并构建着自己的目标感,锻炼着关键技能,培养着自主性,学习着真实的知识。当你将教育变成一项标准化的事情来做时,你就剥夺了他们深入探索的机会,剥夺了学生们掌握独特能力的机会,也剥夺了他们为自己创出一条发展之路的机会。而正是这些东西,才能让他们在这个创新的时代茁壮成长。